我们的历史书,总是忽略99%的普通人
历史学家王笛是一个毫无保留的人,谈生活、谈学术、谈茶铺,他都尽量用容易听懂的表述。
1980年,历史学家隗瀛涛在课上生动而深刻的讲解,让当时在四川大学求学的王笛决定主攻中国近代史。他的第一篇论文写的是辛亥革命。课余,他在报上发表杂文,就着路灯读《射雕英雄传》。日后,他在美国讲课,每当涉及中国宋明城市生活史的部分,都会提起过去被禁的《金瓶梅》。
他赞同美国历史学者海登·怀特所提出的“语言学转向”,认为“历史学作品与文学实际上有着类似的潜在结构,它们并没有截然分离的鸿沟,而历史研究的文学化是赢得大众读者的一个重要途径”。
拉近史学家与普通人的距离,这是王笛在上世纪90年代赴美国读博之后,尤为明显的转变。
他系统地阅读微观史著作,把眼光投向14世纪法国某个山村的日常生活或者16世纪意大利北部偏僻山村的小磨坊主,阅读那些看起来“没意义”的题目,从宏大历史走向具体的民众。
2015年赴澳门大学任教后,王笛通过《躁动的亡魂》指出史学观的问题,“过去研究太平天国运动,我们泛泛而谈死了几千万……但是,死亡不是具体的数字,要从个体的记忆来看那场浩劫带给个体的痛苦”。
他意识到,“历史研究应该有个体的历史”,宏观框架底下是千万个被赶到历史边缘的人。
近日,在深圳龙华书城举办的“对话大家”系列讲座上,王笛以著作《那间街角的茶铺》为例,与读者分享非虚构历史写作的关键,畅谈文学与史学的辩证关系。
借此次机会,我们与王笛聊了聊他的史学观及做学术的经验。
历史研究的下一步,是记载细节
硬核读书会:我们的历史课本基本上是宏观记载,学生需要背诵年份、政策、战争、迁徙等,对于历史的具体场景却记忆模糊。你在《那间街角的茶铺》中提到“写历史需要有细节”,在你看来,历史当中的细节有着怎样的重量?
王笛:过去的历史习惯研究大问题,20世纪前半叶的著名历史学家如吕思勉、周一良、翦伯赞等,基本都是从写通史开始,一进入通史,那就是大架构,写王朝的历史、重大的事件,可以拿来做教科书,但是就比较干巴巴,而且看不到普通人。
这种历史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细节支撑。
我认为写宏观历史要以微观为基础。如果我们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清楚,忽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细节,那么这个宏观框架的依据是什么?很有可能就是依据我们对历史的想象。
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被记载下来,历史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两种历史。一种是历史本身,它实实在在发生,每一分钟过去都变成了历史;另一种就是我们在历史发生以后的重构,根据资料、记录、采访、口述来建构,但是它非常有限。
比如,某个历史时期成都有600多家茶铺,但那一个月里史书上关于茶铺的记录只有一条。多年后,当我们整合资料、重构茶铺时,通过这一条资料来还原的茶馆,与真实历史的差距就非常远。这是历史建构,细节知道得越少,想象空间就越大,靠想象来填补空白。
所以,我主张历史要有细节、有故事,虽然记录始终是有限的,但1/100、1/1000总比1/1000000要好吧。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记录细节,有助于构建宏观历史。
举个例子,以色列记录了上百万个被纳粹杀死的人名,这就是具体细节。我们能提供多少个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字?后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经常拿这个数据缺漏来做文章。如果战后马上在南京做调查,哪怕能记录5万人的名字也好啊。
整个20世纪的主流就是通史,这种框架性的历史已经写得够多了。21世纪,我们要靠历史的下一步——回归细节——来接近真实。中国这么复杂的历史,能提取细节的历史著作很少,远远不够。这需要长期的努力,可能要花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
硬核读书会:你在《历史的微声》中也提到,今天能够看到的历史,“不到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百分之一”。历史是否有不客观的成分?
王笛:历史研究本来就是主观的行为,它不是社会科学。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可以反复被证明的。
比如我研究了一种经济现象、一个物理公式,那么别人必须能够反复证明它,采用同样的方法得出同样的结果。历史不行,如果我把原始资料交给另外的历史研究者来写,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角度了,连题目都不同。
我们的史学观、意识形态、政治观点、教育背景,乃至于家庭出身、经济地位都不同,这些因素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判断。我们一定要承认,历史是有主观性的。
那历史就变成玄学了吗?岂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是这样,这属于历史的不可知论。作为严肃的历史研究者,我们秉承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所说的原则:要写出客观的历史。意思是,客观的历史是一个主观的追求。
历史研究的职业传统就是“不捏造历史”,资料上没有这样写,我们绝不能自己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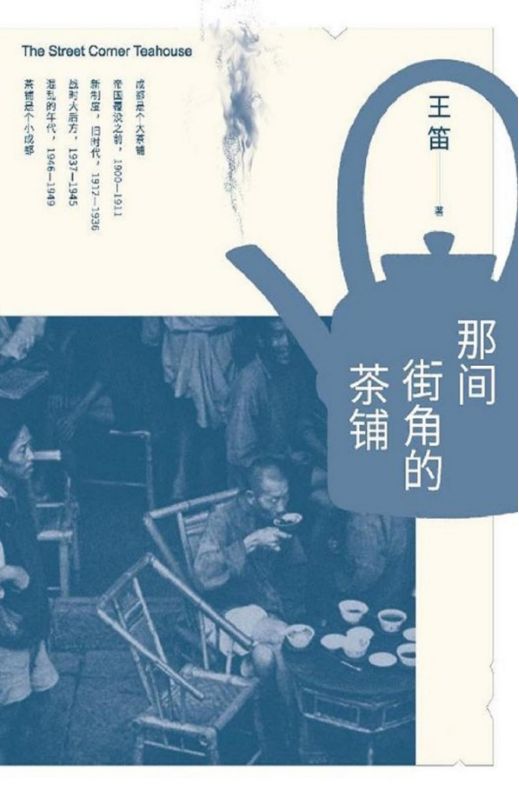
《那间街角的茶铺》 王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10
虽然《那间街角的茶铺》区别于严肃的历史著作,属于非虚构领域,我也不会因为它不需要每一条都作注而胡乱编造,我写的每句话都有根据,否则就会违背我心里边的标准。
所以,历史并不是不可知的,至少,我们的追求是写出一个接近真实的历史。
不要忽略99%的普通人的历史
硬核读书会:你在书里提到,中国人关于茶叶的写作汗牛充栋,但是关于茶铺的写作就很少。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偏差?这是否说明我们的历史研究更侧重于经济或者政治,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层面?
王笛:茶叶是过去中国重要的大宗商品,经济史记录了很多。而且文人也喜欢描写饮茶,包括王安石、郑板桥等,想想看《红楼梦》里边有多少描写是关于茶的,什么茶要配什么水,之类。但是历史上没有一个“公共生活”的概念,人们也想不到去记录茶馆。
过去觉得街头没什么好值得研究的,都是些小商小贩。补锅的、算命的、掏耳朵的、弹棉花的、做爆米花的、做面人儿的,等等,三教九流,组成街头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没有人认为这是历史研究应该做的事情。

成都街头。(图/《那间街角的茶铺》王笛 绘)
像这种关于日常生活的小题目,过去被称为“无意义的题目”,一直面临着被质疑的挑战。事实上,普通人也值得被历史记载。
比如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就是普通人的历史。多年以后,如果要研究2023年快递行业的状况,这本书就是非常好的记录。作者胡安焉作为个体也许不重要,但是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和他有相似的经历,都面临着书里所写的困难、挣扎、社会环境,这就是它的价值。
这是我的史学观的变化——从帝王英雄史观到日常民众史观。
即便帝王英雄,他们的影响在历史长河中也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难道我们的历史就只记载这1%吗?它能取代剩下的99%吗?一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难道不值得被研究吗?我们要写出一个平衡的、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就绝对不能忽略这99%的大多数人。
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写一个意大利中世纪的磨坊主,如果作者不研究,磨坊主这个群体就可能永远被埋没了,但是一旦写出来,他在意大利中世纪的农民就有了相当的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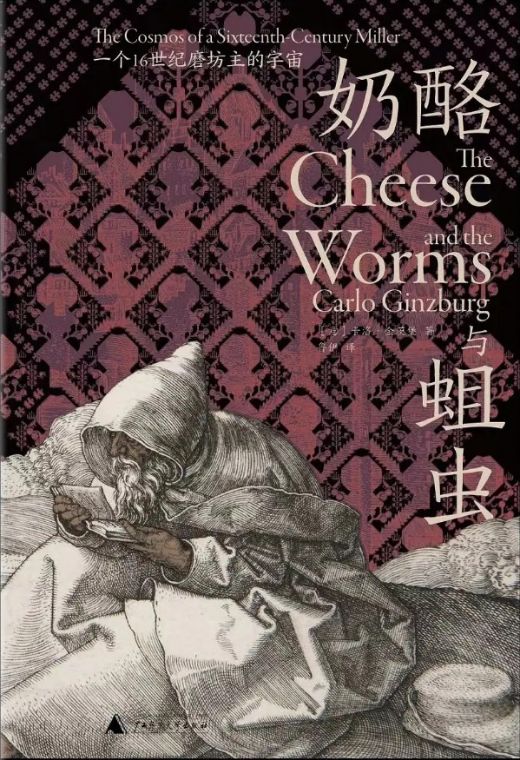
《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 [意]卡洛·金茨堡 著,鲁伊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7
硬核读书会:你这个转变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转变。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就是所谓“无意义”的街头文化,但那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史学观的问题,后来《历史的微声》全面阐释了我的史学观:我的知识来源是什么,到底哪些研究对我有影响。
最后,我在那本书的结论部分打破了我们从小学就在讲的问题——如何找到历史的规律。我的观点是历史没有规律。我想通过它来告诫每个手上有权力的人,不管权大还是权小,在运用权力时一定要非常小心地尊重历史、敬畏历史。
硬核读书会:《那间街角的茶铺》里有一句描写:“每天成百上千挑水夫用扁担挑两个水桶从城门洞出来……如果挑水夫不工作的话,那情况就相当不妙,整个城市的日常生活都会停顿。”相对于帝王来说,民众是一个弱者的角色,但弱者也有可能改变大局面,弱者也有声音、有武器。民众是否也能刺激宏观历史的发展?
王笛:那肯定的,而且理解宏观要在微观的研究基础之上。过去我们写辛亥革命,一般都讲孙中山、同盟会、武昌起义,但是,当革命在地方发生的时候,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以成都为例子,革命是由保路运动引发的,而保路运动又是因为清政府对和平请愿群众的屠杀而爆发,也就是成都血案。过去我们不研究民众在革命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在街上烧香、叩头、拜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生前是同意川汉铁路民办的,所以他们在街上修建,大祭台,端着光绪皇帝的牌子,用宗教的仪式来表达政治的诉求。
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很多类似的现象。比如1925年的五卅运动,就是由上海一家日商纱厂的几个工人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事实上,从辛亥革命开始,民众就参与进来了,但他们始终偏离于过去的革命叙事。
过去总是围绕着孙中山或者立宪派来讲,民众在辛亥革命中是缺失的、看不到的,好像没有起什么作用。好多人都说辛亥革命已经研究到头了,但是我的《街头文化》最后一章“街头政治”提供了新的可能,采用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大众的宗教仪式来看政治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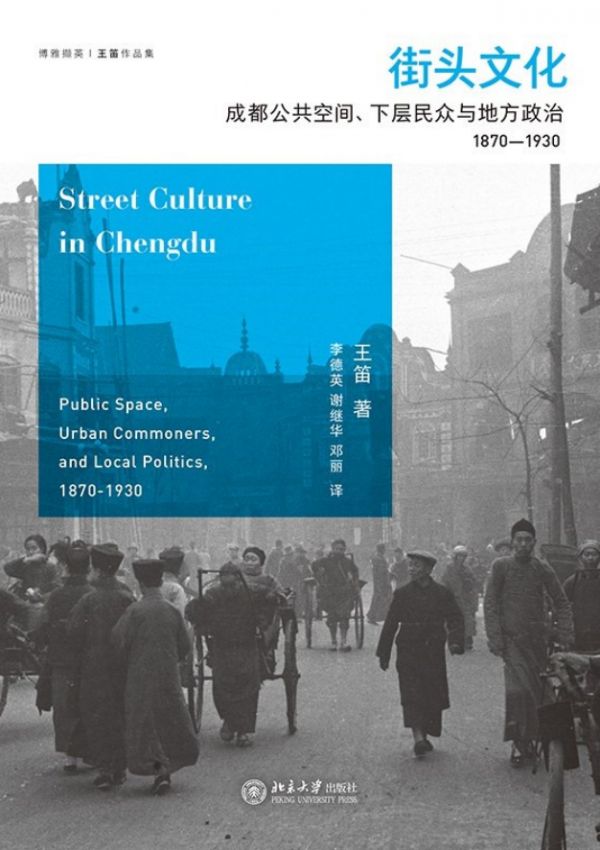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1870—1930》 王笛 著,李德英、谢继华、邓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6
一旦我们的思路转化、方法转化,而且多学科交叉,很多看起来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的题目,就又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做学术就像爬坡
硬核读书会:学术研究是一个长期工作,资料也不好找,有时候坐一整天都没有收获。在做学术的过程中你会感觉到焦虑吗?
王笛:其实是有的,但焦虑也比较短暂。
我研究茶铺前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前期不知道去哪儿找资料,这种时候确实焦虑,因为资料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完成这个课题。包括读缩微胶卷的时候,一页页地翻,有时候一条有用资料都没找到,所以肯定会有那种不知道能不能完成的焦虑。
后来我在成都市档案馆翻阅档案,发现很多没有引起关注的、没人使用过的资料,都是一些很好的线索,如此追踪下去,很多东西就“哗”地浮出水面了。我形容它是个大金矿,当时就有了一种兴奋感。
兴奋之后就是写作,这个过程也有焦虑。因为一写就是很多年,《茶馆》第二卷从写作到修改、出版花了整整12年,有时候做着做着就厌倦了,而且写到一定程度之后总会遇到瓶颈。

吃闲茶。(图/《那间街角的茶铺》王笛 绘)
比如《茶馆》第二卷的前半部分是根据档案来写,后半部分是根据我的田野调查来写,完全是不同的风格和资料来源,怎样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怎样回答人类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的问题,这都是瓶颈。
感觉就是在不断地爬坡,爬到一定程度可以喘息了,却又面临另外一个坡,就这样不停地走。
所以,12年当中,只想赶快把这个事情做完,放到脑后,然后开始其他题目。比如袍哥这个题目,我酝酿了那么长时间,资料也收集齐了,很想马上转移到这个新课题上来。12年不断地做茶馆的题目,已经有点精疲力尽了。
最终还是靠一种自我支撑,既然题目都做到这儿了,就把它做到最好。
硬核读书会:做学术常常要处理大量的资料,尤其你又是研究微观史的,《那间街角的茶铺》查阅了很多访问资料、报刊、档案、小说、竹枝词等,从查阅到书写的这个过程,你是怎么梳理信息的?
王笛:我觉得一般的步骤是这样,当你决定一个大方向之后,先去读二手的研究。
我不赞成那种直接告诉学生“先去找资料”的方式,特别是现在资料数字化了,不再像过去——谁掌握了一手资料谁就掌握了历史。民国时期是这样,傅斯年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过去的历史研究就是史料决定一切。
现在不一样了,数字化使过去很难找的资料变容易了,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了解课题的学术状况,了解这个课题有些什么研究,有了学术的准备之后,就会有问题在头脑中浮现,这时候再去找资料。
如果思路没打开就收集资料,很可能看到资料,都认识不到这个资料有用;思路打开以后,就会发现有些资料好像跟某个具体问题关系不大,但换一个角度看,就很有关系了。
这要求我们收集资料的范围必须非常广,越多越好。
我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学术领域时,收集资料都是靠手抄卡片,然后把它分类;现在处理资料的手段好很多了,有电脑、有复印,可以自己建立资料库。
资料拿到手之后,不要直接进入写作,我对学生的建议是先阅读资料。资料是不会说话的,过去说什么“有图有真相”,其实我觉得图里边都未必有真相,不要以为只要一拿出原始档案,别人就可以闭嘴,没有这回事情。
档案中间作伪、臆造的情况非常普遍,更不要说日记了,要批判性地使用资料,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思考,到底这个资料为什么会这样记载这个问题。阅读过过去的学术研究,眼光已经不同,头脑中也有学术准备了,我们就不至于读半天都不知道这些资料是什么意思。
另外,如果只提取支持自己观点的资料,也会有非常大的缺陷。当我们遇到不支持自己观点的资料时,一定要仔细想想为什么,而不是直接回避它,如果回避了,就很可能失掉一个好机会去发现后面的问题。
所以,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要不断提问题、做笔记,当资料涉及的各种问题越记越多,全部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知道自己到底要从哪里入手了。
写作的时候,我认为一定不要带有任何观点,先把历史的叙事写出来,把事情原原本本地交代出来,它是怎么发生的,发生的过程、结果是什么,把事情梳理清楚以后,再回过头来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而不是先有了观点,然后来证明这个观点。
我反对那种先有观点,然后去找资料来证明自己的方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偏见的一种做法。
虽然历史始终都有主观性,但一定不要带有偏见,如果没有公允地、带批判性地使用资料,就有可能歪曲历史本身,甚至歪曲这个资料本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许峥,编辑:谭山山
相关推荐
历史书上说,赛博朋克的起点是 Facebook 发币
普通人的“捷径”:用笨功夫“死磕到底”
韩国房产,一场普通人的生存豪赌
为什么我们总是晚睡?
创业一年,To B创始人:我们99%会挂掉
淄博烧烤,一场普通人的市井生活保卫战
娱乐:一种容易被忽略的国家软实力
我们总是感到无聊该怎么办?
为什么我们总是苦恋不爱我们的人——心理学给你解答
B站,被音乐人忽略的“应许之地”
网址: 我们的历史书,总是忽略99%的普通人 http://m.xishuta.com/newsview9137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