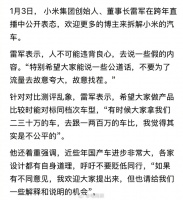一个青海女孩的选择:告别“狗屁工作”,回村过向往的生活
一个来自青海偏远山区的女孩,考上大学,去上海工作,改变了命运。这是小松前25年的励志人生。
但就在一切看似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时,小松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去上海收入还不错的工作,带着她的小猫降薪去山东农村工作。
在社交媒体上,乡村生活常常能收获流量上的嘉奖,一定程度上“回村”还是踩中了某种时代情绪。但如果关掉视频滤镜,真正将生产生活搬到农村,那会是另一回事。人不仅要承受身体劳作带来的肌肉酸痛和皮肤晒伤,还要承担一定的精神压力。村里缺乏娱乐,熟人社会,看天吃饭,回报期漫长。那些回到村里的都市白领,大多没过太久就又回到城里了。
逃离大山,当城里人,在很长时间里曾是小松的人生课题。她的老家是青海——不是那个靠着大海的青岛市,而是挨着黄土高坡和青藏高原的青海省。青海狭长山谷的村子里,坐落着小松的家。
那里有满山的松树、柏树和白杨,有大片的格桑花,地里种油菜和小麦。小松上中学时,整个镇子一个年级只有不到50个学生,去最近的县城要坐三四个小时的客车。小时候,小松家喝的水一直都是妈妈从一公里外的小溪泉眼那用扁担一桶桶挑回来的,后来是挖地窖存水,三四年前村里才通了自来水。

每年春节小松都要去家附近的山上看日出
可以说,小松深刻地理解农村意味着什么。
小松是在一个乡村博主的“感召”下来的。“他们跟那些靠账号变现的博主不一样,是真的在线下做一系列乡村探索。”
小松的老板是一对曾在大城市工作的夫妻,3年前他们回到临沂老家,改造了村里的房屋和小院,期间尝试做一些自然活动,带很多城市家庭感受乡村的美好,今年,他们租下了一片农场,从回村生活变成回村创业的状态,事情太多,人手不够,于是在自己的账号发布了招人视频。
小松就来了。她觉得这可能会将她从工作的无意义感中拯救出来。在如此不确定的时代里,“搞钱”几乎已替代“意义”成为新的工作伦理共识。而非富二代的小松,从山村走出来的农家孩子小松,身高150cm体重80斤的娇小小松,双非本科毕业的小松,仍然认为听从内心的声音,找寻想做的事,是很重要的。
虽然,这种听从内心的代价,是成为父母眼里的“失败者”。在上海工作时,父母可以骄傲地向亲友讲她的故事,但现在,他们对女儿满怀忧虑。
我也忍不住好奇,一个好不容易走出农村的女孩为什么又要回到农村?以及现在的乡村探索到底都在忙些什么,它能给年轻人带来什么?
小松的经历也许能回答以上问题,以下是小松的讲述:
“毫无意义的工作”
刷到“春天一家”这个账号的视频时,我在上海的一个社区图书馆里看书。视频很短,只有四分钟,但我看的时候心咚咚跳,非常激烈地斗争。
春天妈妈说,他们想探索年轻人在乡村除了安居是否还能乐业,他们希望招的人热爱乡村生活,有乡村生活经验,辅助他们运营账号。
我关注他们很久了,看完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我的梦中情工吗?很激动,但也在纠结,要辞掉现在收入还不错的工作吗?这个事可不可靠?我父母不同意怎么办?如果失败了再回来是不是很难堪?和男朋友异地怎么办?这些统统都哗哗哗过了一遍,然后内心的声音还是说想试一试。
当时我男朋友也在图书馆,我把他叫出去,我跟他说,我想换一份工作,要去村里工作。我不知道为什么很激动,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你想去就去,我支持你,做你的后盾,听他这么一说,我哭得更凶了。

后来到村里,小松胆小的猫咪会上房了
那时候我的工作是在一家公关公司做文案策划,工作的大部分内容是重复消耗的,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我好像丧失了很多生活的希望和热情,工作与我而言似乎就成了一个谋生手段。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大学我是从青海考到了南昌,当时我觉得我以后一定要成为一个行走在CBD的高级白领,我要穿高跟鞋,我要坐飞机,我要天天开会,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毕业前我做了四份实习,有新媒体运营、大厂的内容运营、会计和财经编辑。其中大厂的内容运营是反差最大的。刚去大厂时,我很兴奋,觉得大厂真的好有牌面,福利好什么都有,天天挂个工牌打卡,连看门的保安我都觉得很帅气。当时我真的觉得能在这工作是无上的荣耀。
后面我离职的主要原因是部门leader,他是那种要你为工作牺牲所有的领导。有次我做一个海报,反反复复改了很多版,最后我改到晚上十点多发给他,我等了会儿没回复,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就回去了。
那会儿我住的地方离公司4公里,房间只有六平米,没有窗户,每天骑车上下班。我骑到半路,他给我打电话说还要改,我说我已经骑车回家了。他说:“没有我的允许,你为什么回家?这就是你对待工作的态度吗?”
一顿说教给我说蒙了,最后他说你回公司改,今晚就要赶出来。我就很崩溃,边骑车边嚎啕大哭。
这次经历,让我对大厂没有了滤镜。后面我接触到了一个财经编辑的兼职,一个老师带着我写稿子,给我稿费。那是一个很小的自媒体,但从那份工作我学到了很多。我能借此了解商业社会,开拓认知,自己的输出又能被人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
这份实习后,我就没考虑过考公考研,也不想做会计,直接奔着做财经作者去了。毕业后,顺利在上海找到了一家自己一直喜欢的媒体。这份工作一开始月薪八千,因为我表现很积极,半年里涨了三回薪,到年底月薪是1万2。
但在这个过程里,我逐渐认识到一个真相:工作就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最大的意义是赚工资。

每个月写六篇稿子四篇都是广告文。广告文很磨人,没有什么发挥,就是翻来覆去地完成客户的各种要求,消耗很大,成长也在降速。
然后我就跳槽到了一家头部公关公司做文案,收入又上了一个台阶。毕竟如果说工作就是为了赚钱的话,那就找一个薪资更高的。
这份工作更是流水线,规划的海报、领导的发言稿、产品发布会的通稿,都是很套路的工作,每周都会经历无数次驳回,每天都是无限反复地沟通和开会,几乎不需要人的自主性,那点想要释放的创造力也慢慢被磨光了。
毕业两年,我的收入算不错,但其实人很焦虑。在巨大的商业机器运转里,我只是一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我不想一直这样下去,我想做感兴趣的事情,但我又想赚钱,很矛盾。
“大山的女儿”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家在青海,好多人都以为是海边那个青岛,其实我们在黄土高坡和青藏高原的交界处。
我的家乡比大部分农村都要落后。
我们村子在山谷里,沿着山谷,一头到另一头有二三十公里,稀稀拉拉没多少户人家,整个镇到我念中学时也才50个学生。离县城很远,客车在盘山公路一圈一圈地开出去,要开三四个小时。小时候,我们村家家户户种油菜籽,种蚕豆,一年收入三四千块钱。后来整治环境,防沙治尘搞绿化,村里家家户户又种树苗、卖树苗,收入比种地高,过得比以前好了,村里人盖了新房买了新车。
但村里一直都缺水。小时候,不管冬天还是夏天,我妈都要走一两公里到一个沟沟,那里有个泉眼,还挺陡峭,她用扁担挑两桶水回来,那就是我们的家庭用水。到现在,我们村里也是上旱厕,上完厕所拿土埋一下。
我是去县城上的高中,发现城里的孩子他们穿得好,零食多,看过很多动漫和小说,我都没见过。冬天他们家里有暖气,我们村里还是生火做饭。高一那年很自卑,我妈当时给我灌输的思想就是,好好学习,以后要去城里工作,住楼房。

小松站在长满格桑花的家门口
去南昌上大学时,我很多东西都不懂。不会用Word、PPT和Excel,我舍友被我问烦了说“你不会百度啊”,我还真不会百度,我连搜索引擎都不会用。
学习也是,我还是保持着高中那种非常刻板的教条主义去学习。大一有门思修课,我不知道什么是划重点,也不知道问师兄师姐,我就把整本书背下来,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去操场背书。结果考试出来,我是全班倒数第七,我感觉世界都崩塌了。
我一直接受的教育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摆脱乡村,想去更大的地方。
我一步步走出了大山,靠着自己慢慢摸索,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原来觉得高不可攀的东西也接触到了。不知道是不是离家越来越远,曾经想逃离的大山反而成了我一个心灵的栖息点。
从小我就是玩泥巴,爬树,上山,玩虫子,下河,打沙包,跳皮筋……这样长大的。工作后,我每年最期待回家看看,我想看家乡树木的变化,看看我妈种的菜、养的花,想去家后面的小山坡坐一坐。在上海的时候,南京东路当然很繁华很好,但我更喜欢看云看天,看日出日落,拍小区里开炸的玉兰花。
后来,我总去看各种乡村生活的视频,羡慕着别人。但是我不可能抛下一切去村里躺平。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春天妈妈的招聘视频,我感觉自己新生的机会可能真来了。
领工资,拍“向往的生活”
私信春天一家后,我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后来我看到他们近期有个粉丝见面会,我想着与其在上海忐忑,不如实地去一趟聊聊。
当时正好五一,我没抢到火车票,坐客车去的临沂。本来六七个小时的车程,因为堵车,花了20个小时才到。见面之后,我聊了聊自己的基本条件,他们跟我讲了讲接下来的规划。我觉得他们跟视频里没太大差别,很真诚,很有情怀。
回去之后我就确定了,我要来。但是春天爸妈很纠结,他们觉得我还很年轻,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赚钱,他们怕耽误一个年轻人。我说,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起做这件事。
今年6月,我真的来了。
临沂这个村子跟我老家不一样,没有山,很平。这里种一季水稻,一季小麦。村子里大部分都是老人,年轻人多外出打工了。村里的路窄窄的,两旁种着高高瘦瘦的白杨树,春天会飘絮的那种,跟我老家一样,不像上海都是梧桐和樟树居多。
我就住在村里,跟老板一家一起生活,包括吃住。他们给我单独腾了一个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有一扇能看到小院的窗户。

住在村里的房间
我还把我在上海养的小猫花花也带过来了。花花刚来的时候很胆小,躲在屋里不敢动,春天妈妈说它没意识到自己是个动物,更像个可爱的布偶。后来它越来越大胆,会在房顶的红瓦片上散步,会爬树,还好几次把战利品青蛙、虫子带回屋,跟我炫耀。
村里的生活很充实。我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有活就干,没活歇着。做活动的时候,我各个环节都要参与,比如写公众号推广、准备物料、策划活动方案,活动当天我要满场拍照片和视频。
有时候也干一些零碎的体力活,比如做手工、割草、搬石头、做饭刷碗、打扫院子,有时候还得看孩子,一天不知不觉就过完了。每个时刻都在干具体的事,经常上一秒在农场挖沙,下一秒就在音乐会,上一秒在谈合作,下一秒去赶集,上一秒在剪视频,下一秒在喝老板鲜榨的葡萄汁。
当时间被充满后,焦虑就少了。
在村里,没有楼房的遮挡,总能看到绿色田野上方各种形状的云,也常能看到阳光冲破云层射出一条条光线的丁达尔效应。老板家啥都有,桑葚、葡萄、橘子、西红柿、南瓜、黄瓜,我实现了水果自由。
最近我跟着老板去买拖拉机。因为农场之后要搞共享菜园,得把菜园的地平整好,如果总是请人来耕,那成本很高,不如直接自己弄。我们去的是徐蒲坦村,这里是国内最大的二手农机交易市场。
去之前,我以为是什么大型厂房或者明亮展厅,去了之后发现交易市场就在村里,路两边的地里密密麻麻都是拖拉机。帮我们挑车的大哥,讲了很多拖拉机市场和各种品牌背后的故事。我想起了以前自己写商业文章,常常是坐在电脑前搜集二手资料,现在到村里来了,倒是听到了很多一手新知识。
我们前段时间要办一场森林音乐会,需要做一些蘑菇道具。当时来了几个志愿者帮我们一起做,他们有人是从很远的地方开车过来帮忙的,晚上就在这住下,院子里搭一个简易帐篷。大家围在一起做手工,有说有笑,给做好的蘑菇涂红,再画上白点点。这个过程,我都觉得很治愈,能体会到人与人的连接。
我有时候都有一种恍惚,我仿佛是领着工资,来过“向往的生活”了。当然了,乡村生活有岁月静好的一面,也有很忙很累的时候。

花花会爬树了
之前我们做一场水稻科普的活动,就是告诉城里的小孩我们吃的大米从何而来。活动在田地里举行,我要做活动记录,就得站在泥地里拍摄。水没到膝盖,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我的脚底划破了。
但大家都在忙,没人能顶替我的工作,我不可能不干,我就一直忍痛完成了那天的拍摄,回来洗了一下脚,贴了个创可贴。第二天活动继续,我还是要跑到地里拍,到下午脚底伤口就发炎了,伤口肿痛,走路我都龇牙咧嘴的。
两天的活动结束后,我完整地休息了一天,脚后来慢慢也恢复了,只是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想说,脚底划破真的太难受了。现在每天忙得没空刷朋友圈,只有临睡前有空翻一翻,一沾枕头就着。
在乡村做事,回报周期很长
我爸妈到现在也不太能理解我的选择。
我妈打电话时会拿我一个发小处处跟我对比。说我发小工作稳定离家近,再看看你。说实话挂掉电话我很失落,从小到大我都被拿来跟发小对比,家务要做得比她好,学习要好,找的工作工资也要比她高。现在我回村了,没有那些响亮的title,我成了妈妈眼里的“失败者”。我爸更是直接说不知道你在忙啥,你要种地,回家我给你包两亩地种。
可能因为我跟老板是同频的人,我加入他们,跟在上海打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更像是跟着他们一起创业,是他们的合伙人。这种情况下,工作起来,你就不会计较利益的得失。焦虑也跟上海的那种焦虑不一样。

我最近正因为视频流量不够好而焦虑。
尽管我老板不依靠自媒体赚钱,对账号的商业化没有追求,也不想追求热点,只想平实记录。但它毕竟是一个宣传的窗口,是他们花三年打造的一个IP。我工作的价值,最直观的也是体现在账号的数据上。数据不好,我就很有压力。我老板总会安慰我,我们会有被看到的一天,只是现在可能还没到时候。
说实话,来这里之前,我从来没有独立成体系地运营一个账号,更多是自己弄着玩。现在我要专门学剪辑,要研究怎么做内容,怎么挖掘他们乡村生活里的点,给呈现出来。
前几天还有个粉丝过来,他刚从字节离职。他来之前,我跟老板挺焦虑,因为怕他劝我们怎么追逐热点,但他没有。他来了之后,就是跟我们讲了下现在抖音的算法,顺便给我们打打气,鼓励我们坚持做自己,不要气馁。
经常会有各种人来拜访我老板。有人是在乡村做民宿,有人也是在做农业,他们从成都、江浙各种地赶过来,为的就是当面坐在一起聊聊天,互相汲取力量。我发现他们都很有情怀,他们更关心的是怎么种出更好的食物、怎么让乡村发展起来,而不是说我要一年赚多少个达不溜、我要买几套房子这种。
我原本计划在这里待一年,如果做出点成果就继续做下去,不顺利大不了就回上海继续找工作。但两个多月待下来,我觉得一年太短了,什么都看不出来,我可能要待得更久一点。
在乡村做事情,它的回报周期很长。
它不像做知识付费卖个课这种,我们是真的把钱砸在土里,你要一寸一寸地开垦,要拔掉杂草,平整它,要翻肥,要等春去秋来,才能迎来收获。然后你才能吸引人来体验,来买你的服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资产的投入。我老板回村三年,每天都忙得团团转,但实际上他们还没盈利。
有时候我也会怀疑,现在这样的市场,我们做这样的亲子互动、自然教育,真的可以吗?
且不说生育率越来越低,孩子越来越少,就是家长愿不愿意往村里花钱呢?周末孩子都在忙着补课、上培训班,父母更愿意把钱花在这些地方,他们希望孩子考好成绩,上好大学。

在村子的田间做自然教育
而我们在做自然教育,想让孩子感受自然,了解大米和面粉从哪来,知道蔬菜长在地里是什么样,坐在田野里听一场音乐会。虽然很有情怀,但我们知道它不是那么现实的东西,也不是那么紧迫的需求。
参与两个多月以来,我也体会到靠天吃饭的那种不确定性。前段时间筹办了很久的森林音乐会,如期举行,有100多人来到了农场。结果两场大雨,让活动不得不中断取消。
后面为了弥补,我们说在小院里再补办一场音乐会,提供晚餐,增加新的活动内容。但是原本报名的40组家庭,最后只来了十来组,其他人都退款了。整个就是一个亏钱的大动作,成本完全没有收回来。还是挺失落的。
当我不把这份工作当个赚钱手段,把它当成事业的时候,快乐和烦恼的浓度都会成倍放大。
我还是觉得,人把一天里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哪里,很重要,这个时间要花得有用,而不是花在一个几百字的方案改七八百回、一遍遍推倒重来里。
小时候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是被父母和老师塑造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我对什么感兴趣,我喜欢什么,我没有概念。我很庆幸我能考上大学,走出大山,虽然这个过程中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可是也点燃了我内心的小火苗,让我有想去找寻的事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OSS直聘 (ID:bosszhipin),作者:迟文,编辑:贾嘉&白话日报
相关推荐
短视频里赶大集:宇宙的尽头是回村
孤独后厂村:30万互联网人跳不出的中国硅谷
不想在大城市买房的日本人,过上了“游民”生活
00后的神仙工作:上山、去非洲、当保安
月薪一万八但没意义的工作,你愿意干么?
为了逃离内卷,这届青年选择“反向生活”
逃离工位以后,我们能摆脱工作倦怠吗?
那些清北毕业生,回到了教培工厂
5年打了20份零工,我不再追问工作的意义
县城新中产:拿三线工资,过一线生活
网址: 一个青海女孩的选择:告别“狗屁工作”,回村过向往的生活 http://m.xishuta.com/newsview884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