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主义者的底层政治逻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标题图来自Unsplash,原标题《学者罗新:网络民族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
在最近出版的学术随笔集《有所不为的反叛者》当中,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指出,在现代知识洗礼下,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已经意识到,“民族”的本质是一种政治体,而不是其所宣称的、一种源于共同祖先的社会体;“种族”或者“人种”的概念也不具有任何科学性,应当被废弃。但是在今天,民族主义和种族论都颇有市场。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许多“网络民族主义者”在公共空间蜂拥而出,彼此取暖;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DNA技术也被用来探讨族群差异,推出新版本的种族思维。
面对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沉渣泛起,罗新反思了历史学对历史的责任问题。他举例道,纳粹德国不是希特勒凭借一己之力制造出来的,历史知识也是制造他背后的种族主义等思潮的原料之一。与之相似,今天大量“网络民族主义者”的激烈言辞也源于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历史学自己发展出来的教条、观念或者常识。因此他认为,历史学要对自己时代的历史负责任,历史学家的使命就是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去反抗、去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
实际上,在种族和种族之间、族群和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画出一条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早在2014年出版的《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中,罗新就从北魏皇帝的即位仪式入手,强调了历史研究的内亚视角,提出历史上的游牧内亚和农耕中国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去年,他因《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一书而被许多普通读者认识,这本书被历史学家陆扬称为 “1949年以来大陆地区写的最好的一本游记”,罗新说,写作这本游记时,他写来写去,就是为了写出人在历史夹缝当中的艰难处境。在此次界面文化对罗新的专访当中,他进一步强调,人群和人群之间不可能存在清晰的边界,所有的人群都是崭新的: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一个崭新的民族。
1. 不能为了现实的、具体的、短暂的目的去编造历史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批判传统历史学的“起源崇拜”和“迁徙崇拜”。能否讲一讲“起源崇拜”和“迁徙崇拜”对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罗新:历史讨论时间问题,总要追溯到时间的源头。任何问题、任何事件、任何人群,都要说到起源。里尔克有一首诗,讲一个平凡旗手的死亡,他说:“一刹那把另一刹那抛弃了。”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每一个时刻都是在起源,每一个时刻也是在终结。我们在叙述里特别喜欢寻找遥远的起源,并且喜欢把遥远的起源和后来特别是现在的状态联系在一起,用起源来解释我们现在的状态。这是传统历史学的基本方式,也是人类的思维的方式。比如说一个人很高,我们就会推测他的父母很高,进一步推测他祖先很高,可是这中间其实有无数的变化的可能。其实,起源和今天没有关系。
另一个是迁徙崇拜。在讨论人群历史比如说民族历史的时候,迁徙崇拜认为,一拨人会完整不动地经过长途迁徙来到另一个地方,这是不可能的。迁徙的过程当然有,但是这个过程在经过变化,有的人离开,有的人加入,旧元素消失,新因素出现,才会有今天。我们在今天还在迁徙,这么多北京人哪里来的?几十年前北京才几十万人,现在几千万人,当然是迁徙的成果。又比如说,今天我们不能说美国人都是从英国五月花号的后代,五月花号的后代现在还有多少我都很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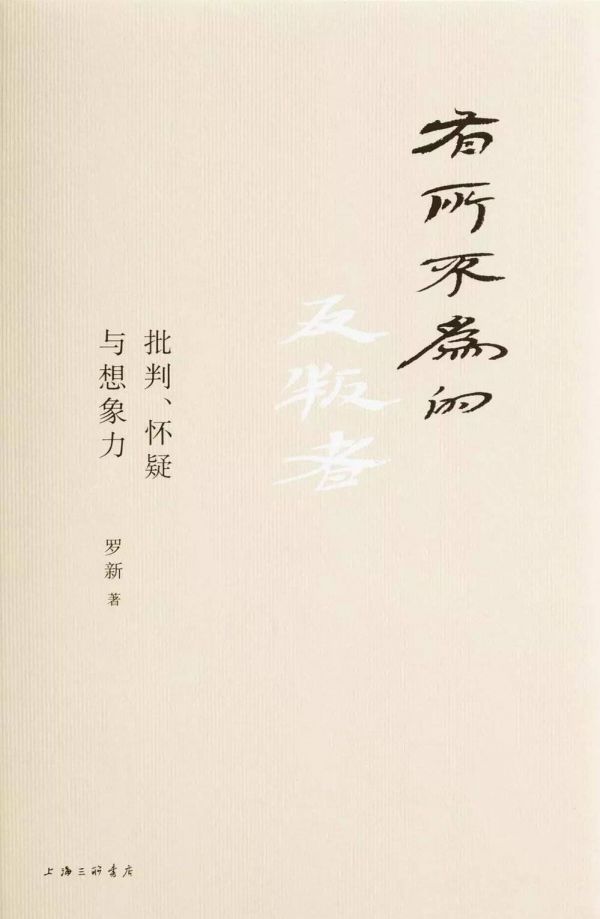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罗新 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 2019-5
界面文化:为什么人们要强调这些?
罗新:因为这样可以强调一个民族血统的纯正、高贵和遥远。比如说,希特勒说日耳曼人是古老的雅利安人的后代。其实不管有没有雅利安人或者日耳曼人,古代任何人群都在不停地和其他人群进行基因交换、文化交换等各种交换。有旧成员的离开和新成员的进入,人群和人群之间剧烈的交换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存在,人群和人群之间不可能存在清晰的边界。
但是我们在叙述的时候总是强调有边界。一是强调时间上的起源,一是强调空间上的迁徙;不管时空相隔有多大,人们还会相信一群人可以完整地成为今天的另一群人,或者可以用那样的时间空间上的另一群人解释当前的这一群人——历史不可能是这样的。
我想强调,现实生活中没有古老的人群,所有的人群都是崭新的。今天我们是一群人,明天我们会分散,变成新的人群。中华民族不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一个崭新的民族,是到近代社会才形成的民族。
界面文化:你提出要走出民族主义史学,但你似乎也在反思那种“超越族群民族的共同identity的呼唤”,为什么?
罗新:这涉及到历史学的另一个意义。人们意识到应该建立一个共同的、超越了政治构造的认同,通过建立这种认同,来消除人们之间隐藏很久的区别感和敌意。例如,很多欧洲左派知识分子强调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身份,因此想要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历史。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这样讲述的历史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为了这个目的去制造的历史,很有可能在原理上和我们想要批判和反对的那些东西是一样的。
历史学不应该为了某一个现实的政治目标服务——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认同,毫无疑问是一个政治目标,这个目标无论是崇高也好,不崇高也好,它都是一个现实的、此刻的、短暂的目标。
界面文化:现在有些学者也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局限,转而尝试探索亚洲的新的可能性,比如说在沟口雄三、子安宣邦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怀,他们某种意义上都在寻找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可能。能否谈一谈你对此的观点?
罗新:我不是说共同身份的建立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做到,我是说,不能够因为要建立它而开始特意讲述相关历史,选出历史当中对此有利的而去讲述。
比如在东亚有共同的命运。我们看到东亚自古以来就有内部斗争,而且越往现代越血腥、分离得越深刻。如果只讲中国和日本只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把血腥历史淡化或者故意不讲,那也不是历史。不能为了眼前的目的去讲历史,历史就是历史。

子安宣邦,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大阪大学名誉教授
界面文化:建立东亚共同体有可能是基于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能否请你讲一讲政治体和文化体的概念?
罗新:政治体指政治构造。中华民族当然是一个政治体,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人群合起来叫中华民族,也就是说划定边界不是因为人们都说共同的语言或者相貌和别人有明显差别。例如,在中国境内的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可是在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族就不是中华民族。造成这种差别的是国家。国家是政治体,所以我们说民族都是政治体。甚至连今天我们以为是族群意义上的、有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汉族,在形成的早期也都是政治体,是一股政治力量,比如说因为秦汉时代的政治发展促成了境内的这群人逐渐变成了互相认同的、文化上有很大一致性的人群。
文化体是有某种共同文化的,说同样的语言、有共同的风俗、有共享的历史。很大意义上,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和中国境外的蒙古族是一个文化体,但不是一个国家。这就是政治体和文化体的区别。
儒家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为东亚地区很多的人群、许多强大的王朝共享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是否足以说明共享这个文化的人群之间必然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当然不是。
界面文化:那么,走出民族主义史学之后,我们要走向哪里呢?
罗新:不为了现实的、具体的、短暂的目的去编造历史,不从历史中抽取某些事实组成新的讲述方式。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讲自己想要讲的历史——你可以讲东亚有某种共享的文化,但是另一个人也可以讲东亚近代以来巨大的分裂和对抗——都可以讲,各讲各的。
2. 互联网时代民族主义达到了很猖獗的程度
界面文化:你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一书中还提到了DNA技术。你指出,在如今西方主流媒体和科学论著当中,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和词语基本上销声匿迹了。但是DNA技术又让种族思维沉渣泛起,这一现象为何会出现?
罗新:在西方社会的受过教育的阶层,人们对种族思维进行了反思,使得这种知识已经被颠覆了,但并非所有人都经历了现代知识的洗礼。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被指责为“白人种族主义者”,说明在美国精英阶层也依然存在这种思维的影响,更不用说那些没有经过种族思维反思的社会了。
在德苏传统(匈牙利考古学家乔纳德·巴林特指出,关于人群分类,在20世纪有两个影响很大的学派:一个是英美学派,强调主观认同;一个是德苏学派,强调客观标准,包括物质文化和生物学特征)下,前苏联的很多地方和中国都没有经历过种族思维的反思。虽然中国在文化传统上不是很重视种族思维,可是一般人也相信人和人之间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差异本身很容易导致价值判断。
如果你相信人群和人群之间有很大不同,就会开始在两者之间寻找差异。可是人群和人群之间究竟是不是存在确切无疑的生物学的划分的标准?这是很大的问题。
近代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的族群思维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群和人群之间的差异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是文化意义、历史意义上的,是不同的历史传统造成了人群的差异。在生物学意义上,个体之间当然有差异,可是群体之间差异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人群和人群的边界是不清晰的——我们今天讲的人群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边界;在民族国家之内,有民族划分的国家又以民族为边界;在没有民族划分的国家则以族群为边界,但是民族和族群也是文化性的。
比如说在中国,你如何确认汉族和白族或者蒙古族之间有生物学上的差异?住在内蒙的两家人,一个在户籍上写汉族,一个在户籍上写蒙古族,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家在生物学上和汉族一样、另一家和蒙古族一样?也许这家蒙古族人前不久还是汉族,到80年代重新划分民族的时候,他们出于某种考虑——例如上学等现实利益的考虑——把自己划分成了蒙古族。如果我们确认了他们是蒙古族,再把他们身上得到的DNA数据当做标准数据,和汉族的那一家进行比对,然后将两家人之间的差异放大,当作是两个人群之间的差异进行讨论,那么这个方向是错误的,可是偏偏有些人就相信这个,拿这样的数据来说明差异。
人们认为DNA技术是最新的技术,觉得这种技术侦测出来的差异表现是最确切无疑的。可是这种差异本来是个体之间的差异,任何两个个体之间都会有差异。因此,这种寻找一定没有结果而且没有意义,是缘木求鱼。

人群和人群之间究竟是不是存在确切无疑的生物学的划分的标准?这是很大的问题。
界面文化:那么DNA技术可以做什么呢?
罗新:例如,现在发现一个古代的墓葬,另一个地方也有古代墓葬,人们相信这两个墓葬相关,认为这群人是从那个地方迁徙过来的,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基因技术进行生物学意义上的比对;如果他们之间有巨大的亲缘关系,可以相信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也有可能我们会发现两者没有关系,这也有意义——他们为什么会被相信是相关的呢?
有人宣称自己是某某人的后人,可是经过DNA检测,发现根本不是;否认他不是某某的后人确实是一个事实,这一事实的另外一种意义也需要认识:他为什么要宣称自己是某某的后人?为什么很久以来人们相信他是?这样的分析可能更有历史学意义。
我有一个小小的判断,个体都有祖先,人群没有祖先。因为每一个人的祖先都是多方向的,由祖先方向各自不同的人构成的人群,方向却指向一个人,在生物学上没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讨论人群和人群之间的差异,例如讨论汉族和另一个民族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这个方向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在这个方向使用DNA技术。避免这个情况,要拥有新的历史学思维,需要质疑和批判。
界面文化:在你的书中我们还看到新技术的发展对民族主义的促进作用。比如说互联网应该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很多人却成为了“网络民族主义者”。
罗新:过去,民族主义者在现实中进行表达,通过出版著作、喊口号、贴标语,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提出抗日主张,都是民族主义的行为。但是今天的网络民族主义不是通过现实生活中的言论和行为(来表达),而是通过网络发言。这种发言在某种层面上是安全的,不需要负责的。因此有时候会表现出更加随意和激烈的一面,激烈到侮辱谩骂的程度。
互联网时代民族主义达到了很猖獗的程度,这是让人意外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政党、政权用某种行政力量来组织的民族主义,而是许许多多的个体在网上互相激励、互相交流而走到一起去,形成了巨大的网络力量甚至是网络暴力力量。这个现象在所有的人群中都存在,不只是在中国。
界面文化:你有想过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吗?
罗新: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社会、在人群的内心有很深的基础。现代民族国家政权稳定以后,由政权主导的媒体、行政组织没有鼓励民族主义,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在控制这些行为的发展,我们觉得(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不存在了,但是网络使得另一个空间出现了,非政府的力量出现了,过去这些力量在生活中是非常碎片的,可是他们却在网络上集聚起来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
现在民间的民族主义的激烈情绪,可能不只是人们对民族问题、对国家问题、对某个国家对外关系的思考。我非常想强调,网络民族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他们的声音在别的方面得不到倾听,利益得不到代表,只是找到了自己认为是安全的发泄口。他们无法表达对很多问题的感受,因此就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毕竟骂外国的表达相对安全。再比如有些人在提到对穆斯林的情绪的时候,发言显得非理性,但是也许这种情绪背后是人们对其他方面的情绪酝酿,比如说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升学没有分数照顾等等。也许在更大的网络空间里这种讨论已经持续了很久,到这个点上,某些言论毫无疑问是非理性的,可是非理性的东西也有它的基础。

网络民族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他们的声音在别的方面得不到倾听,利益得不到代表,只是找到了自己认为是安全的发泄口。
界面文化:这个话题和空间对他们来说都相对安全。
罗新:民间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我们称之为网络民族主义的东西,简单地否定很容易,却是粗暴的。作为现代人要学会去理解其他人说的话背后的意义,他们说这个是不是基于别的原因。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一起生存,不管大家实际差异多大,相互理解是很重要的。
3. 历史没有绝对意义上的重复,学历史就是超越自己
界面文化:一种走出民族主义史学的尝试是时下流行的大历史写作,现在市面上大历史写作非常流行,历史叙述框架很庞大,内容涉及很多学科,但是很少见到专业的史学工作者来点评这些书。我注意到,你在书中也有对大历史著作比如《人类简史》的关注。
罗新:从卖书的角度,《人类简史》是近年来大历史著作当中最成功的,仔细读的话,会很多佩服作者的地方,其中可能没有一项知识是他(指《人类简史》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原创,但他得消化那么多知识,再组织成自己的书,这是了不起的。但是,最终他想要表达的,特别是后来他写的《未来简史》,成为了对未来的预测。其实他在书里也讨论了历史有没有预测能力的话题,但他自己却走向了这一面,很像是有先知情结,在这一点上我很警惕。
近年来的大历史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考古学家罗伯特·凯利的)《第五次开始》,因为像大卫·克里斯蒂安(“大历史”教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些人都是专门做大历史的,但是《第五次开始》是考古学家介入大历史叙述。他说,“第四次开始”是国家,而现在进入到了国家消退的状态,国家体制正在消亡,未来人类会出现新的组织形式,这几乎可以说是20世纪中期以后全球化思维的极致。他看到国家阶段是五千年,这个阶段结束以后该出现新的阶段了。读者接不接受是一回事,也没有太过分。

《第五次开始》[美]罗伯特·L.凯利 著 徐坚 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
大历史观察人类历史的尺度变大,很多东西变得无关紧要了。过去我们思考司马迁生于哪一年,鸿门宴上喝什么酒、吃什么肉。如果我们在很大的时间尺度上来讨论问题,那么这些有什么可以关心的?甚至汉朝在前还是唐朝在前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时间尺度变了。如果讨论一百年,那当然一百年里面什么都重要;可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十万年,关注的问题变了。
界面文化:这样一来,对个人的关注会不会没那么多了?
罗新:历史当然要关注个人,因为历史归根结底是个人的、个体的历史。但是,就像你现在回头看自己小时候的很多经历一样,当时在乎的事情,现在就感到很没有意义。过去我们只想着我们的民族怎么样,国家怎么样,我们和别人之间的领土纠纷、新仇旧恨,现在突然变成这个尺度,那些还有什么意义?这就赋予了你新的历史观。
当然,绝大多数大历史以当下为观察点,起点是宇宙爆炸,讨论生命起源、人类起源、人类进化、智人的出现,你会发现时间尺度在不断缩小,最后归结到工业革命、现代社会、此刻,这样的尺度下,必然以现在为起点。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大历史研究也都把此刻当做转折的重大时刻。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千年以后的大历史学家也很可能根本讨论不到我们的此刻,他们一定认为他们那个点是重大的变化时刻。
界面文化:说到大历史这样的通俗历史读物,不妨谈一谈普通人读史。很多人读史是为了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你认为读历史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吗?
罗新:过去人们读《资治通鉴》,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想要借鉴过去的经历以有益于现实的国家治理等方面。这是过去很容易产生的对历史的理解。
历史没有绝对意义上的重复,前一代人会犯错误,后一代人也会犯。前一代人能做到的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后一代人不一定都能做到。我不相信人会因为了解过去而变得更聪明,但是读历史又是有意义的——意义可能因人而异,因条件变化而异。
对过去的人,过去的人在各种事情里的表现和反映,我们不是在里面寻找经验教训,只是重新经历一下,在这种替代性的、带入性的经验里,某个人的经验就相当于你自己的经历,他/她的痛苦就相当于你自己的痛苦,这使得我们超越自己的经历。学历史就是超越自己。
界面文化: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者对专业的反思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但是社会大众的历史知识总是倾向于滋育历史神话。你有没有想过,究竟怎样才可以填补学术研究和社会常识之间的高度落差?
罗新:落差永远会存在。专业工作和普通大众之间总是会有很大的落差。数学家和我们的数学知识之间落差有多大?简直是两个世界。如果我们可以接受那种落差,我们也可以接受历史学家和普通历史爱好者之间的落差。可是有趣的是,对于文史哲这样的基本人文学科,人们意识不到这种落差,人们认为这些内容都是文字写出来的,都是大家看得懂的东西,因此很多时候会想着去和历史学家对话。不过我们不能像物理学家一样指出自己和普通大众不在一个层面上,无法进行讨论。而且,我们不仅表达方式是普通的、容易被理解,而且我们关怀的问题和大众之间共享的太多了,甚至有时候我们的题目也来自大众的关怀。因为整个社会关心什么,所以我们也开始研究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专业性而和大众区别开来,认为自己很专业,而拒绝对话。我也从大众那儿获得灵感。
过去我不在乎这个问题,以为研究就是研究,而且我研究的时段很早,和现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些现实中的问题,比如十几年以前我和老同学讨论现代边疆的民族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从那之后,我做的很多工作有了更明确的目标,研究方向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比如我开始讨论古代政治体,也就是国家,在扩展过程中对不同人群采用的政策、方法引起的后果。我过去不研究南方,在那之后,我对南方的民族问题也感兴趣了。
由于专业工作分得高度精细,可能我们某一个点上的专业程度让我们难以和别人平等对话,但是在另外一个点上,又和普通爱好者知识基础差不太多。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主动和普通读者交流。这其中,也有科普的一面,把专业认识用比较生动的、容易接受的语言传达给大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潘文捷,标题图来自Unsplash,原标题《学者罗新:网络民族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
相关推荐
网络民族主义者的底层政治逻辑
金融业的底层逻辑变了
哈耶克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产业互联网的底层逻辑
大公司背后的底层逻辑,往往不超过这10个字
2019年密室行业爆发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伪民族品牌
黄奇帆:数字化经济的底层逻辑
买猫爪杯的第n个理由:揭秘星巴克真正的底层逻辑
商业世界的4种底层逻辑:自然、机制、多样性和营销
网址: 网络民族主义者的底层政治逻辑 http://m.xishuta.com/newsview58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