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他们,到底有什么“用”?
尽管以文学为专业,以文学出版为职业,对“文学有无用之用”的标准答案也认可,但我还是会经常忍不住问自己“文学到底有什么用”的问题。这个“用”的困惑,有时候是实用主义的,有时候则事关见识、价值和操守;有时候是关于整体行业“活不好死不了”的,有时候又怀疑文学能不能对从业者的个人修为和道德底线发挥作用;有时候跟文学眼下的社会影响力微弱有关,有时候又跟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贯的人情干扰和评价标准混乱有关。
某些时刻,这虚无和幻灭甚至会让人透不过气。比如,当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里掷地有声地发问:二战时期犹太人集中营里的纳粹官员,是怎么做到晚上欣赏巴赫、阅读托尔斯泰,白天到集中营朝同类挥舞鞭子、释放毒气的?他们信奉的“主义”的逻辑之恶中,是不是也包含着人文知识和人文思考的“恶”?他的意思是,如果人文停留在所谓“文化修养”的表层,而没有转化为尊重、悲悯、敬畏、通达等精神底色,那是不是反而会泯灭人性、滋生对同类的冷漠?
由此难免不让人想到,假如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真的不可或缺,但又不过是另一个儒雅矜持,甚至道貌岸然的名利场,那我们凭什么还认为它距离精神和价值更近?假如它所说的“人学”只代表了人性深不可测、曲晦幽深的那一面,那我们是不是索性如卢梭倡导的一般,回到无所渴求的“野蛮”状态更为适宜?
幸亏,还有一些人、一些书,能让人感受到文学之于个体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并非科班,却珍视文字、珍爱文学,他们的抱负、挫折、不幸……需要文学的解救,他们借助文学认识自我、与现实周旋。文学之于他们,能直接通往生活境遇的改变、生命价值的认知或审美更加精进的阶段。文学之于他们的“用”,直白、坦诚而不可或缺。
《世界微尘里》:一粒尘埃的标本价值
如果不是一次采风活动,我不会认识广东东莞的作家莫华杰,也不会读到他的自传体非虚构作品《世界微尘里》——尽管他已经获得了诸如“漓江文学奖”等奖项,也创作了一些小说、影视作品、散文,在广东已是小有名气,但他依然是我阅读和关注的盲点。
说来残酷,作家的影响力也大致遵循自然界的丛林法则:头部作家如森林里的狮子、老虎,个体即个性,每出一部新作都引人关注,让人不能忽视。其余很多作家,若非作品极其特异或有特殊的机缘,都更需要集群效应,更需要靠文学思潮、文学群体形成现象,产生影响力。
可惜近些年,这方面恰恰很欠缺:一方面是命名缺乏,另一方面是命名无法产生共鸣。跟人群中的“原子化”相呼应,文学界的“原子化”情形也严重——作家都希望靠独立个性而不是与别人为伍傲视群雄,甚至他们也不愿意被任何概念,包括“打工文学”“底层写作”这样的概念框定。
在《世界微尘里》这本书中,莫华杰用自发向自觉过渡阶段的文学认知,用质朴而本真的线性叙述,用略带抒情性的语言,讲述自己从小病痛缠身,在极端痛苦绝望中与文学结缘。
他小学毕业就到广东打工,一路在各个工厂、各种行业辗转,经历过身无分文、露宿街头、被霸凌被诱惑被伤害,也经历过有家难回、爱情失败、更名改姓、明天不可期等至暗时刻,其中,晚上没有被褥躺在光秃秃的床板上,捡漏水的脏饭盆打饭,没筷子用牙刷代替等细节,让人读之触目惊心,忍不住心神恍惚:这到底是21世纪的青年作家所描述的亲身经历,还是19世纪的狄更斯、雨果所捕捉的文学细节?
想到举世瞩目的中国制造中,曾有那么多青春以如此方式参与其中;想到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中,依然有那么多孙少平、高加林、莫华杰们理想昂扬,心中的感慨真是难以名状。后来,他因为给饭店写传单展露才华,终于慢慢靠文字天分脱离了在大厂流水线上徘徊的宿命,过上了“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尽管某些时刻我们也难免担忧,他会不会只满足于变成“文学打工人”而已,但毋庸置疑,文学已经用自己不唯学历、只唯阅历的平等包容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本书腰封上的广告语很励志:“一个身患疾病的打工青年,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知名作家的?”说他“用文学对抗生命艰难”,成就了一本“微尘的生命之书”。
书中的他,思维方式和书写角度的确也很励志——每当他非常绝望的时候,他总是回忆自己的病痛,回忆痛不欲生的身体之疼和四处求医问药带来的病耻感,跟那些刻骨铭心相比,眼下远离亲人和乡亲的潦倒落魄,都只是单纯的“英雄末路”而已,都还能忍受。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工友跟自己一样,更何况还有文学,有作家梦,有阅读,有跟苦难相伴相生的写作天分,有这一切带来的否极泰来、贵人相助、成家立业的现实转机,最重要的,有开朗的性格、不忧郁的自我。
苦海茫茫,文学是他的岛屿,也让他“成功”,让他得以多年后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去寻找旧日工厂的遗迹,如“成功人士”一般追怀自己的青春。这样令人欣慰的结局对一个小学毕业的乡村青年的奋斗故事来说,已经足够。
然而,文学的确也残酷,其残酷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在世俗层面的成功上寄托意义和价值。它不满足于励志,不甘心让一个人的苦难停留在苦与甜的层面而没有典型化和普遍性的辐射价值和延伸意义。
文学总想要更多,“真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层次,或者等级。文学固然厌烦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固然厌烦花哨的技法掩盖枯竭的生活、贫瘠的想象力,固然渴求毛绒绒、硬邦邦、生龙活虎、独一无二的“真”,但在这些之上,它还有更多要求。尤其对立志追随它的人来说,它的要求几乎是没有止境的,以它为岛,也需要做好鲁滨逊般的准备。
人生太苦,若还要在喘息的间隙,再尝提炼苦难、认识苦难的“苦”,实在是不近情理的残忍。当然,对自觉进入文学世界的人来说,后面的“苦”有望变成人间清醒的幸福。

《世界微尘里》,莫华杰/著
海天出版社,2022年11月
《我在北京送快递》:理想主义者的“伟大的失意”
《新京报》在专访胡安焉的导言里写:“这不是一名快递员通过一篇文章‘一夜成名’的故事,而是关于普通人如何在日常生活的荒芜中被阅读和写作托举,在现实世界的幻灭感中步步重建起内心的秩序。”
胡安焉自己也不认同写送快递就是“底层写作”的说法,他说假如“底层”指的是社会金字塔中的层级结构,是芸芸众生,那他认可——近些年来,“底层”和“小人物”的内涵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穷”分为“绝对贫穷”和“相对贫穷”一样,随着阶层跨越的艰难,这两个概念也越来越相对化,曾经所承载的道德感也在减弱。
如果说《世界微尘里》的叙述还在“活着之难”的生存框架里,那《我在北京送快递》的确已经进入了精神困境和自我选择的层级,甚至有点像19世纪初期的波西米亚人。“波西米亚人坚称,即使他们缺乏体面的外表,他们依然因为奉献精神而应该享有最高的荣誉,因为他们具备良好的伦理意识以及感悟世界和表达思想的能力。”(阿兰·德波顿 《身份的焦虑》)
对书里的胡安焉来说,活着也难,缺钱和工作不稳定的耻感一刻也没离开过他,但他有宽容的父母、没有向他施加压力的“熟人社会”,因而他可以在职业里“体验”,在生活里“游历”,也可以不那么“务实”地、“任性”地坚持用自我的尺子衡量工作环境和社会,过一种有心灵态度的生活。
如此一来,他觉得社恐自我的安放更难,在“工作和自由”之间的摇摆不定更难——他的书里充满了自我认识的渴望、深度思考的努力,其中对“自由”的剖析也颇有见地。
他说自己没什么理想,却有点“理想主义”,所以,才会在10年里做了19份工作,辗转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他在书里择要讲述了几次有代表性的工作经历:送快递、做夜间理货员、看便利店、做保安、卖自行车、开网店、开服装店、做加油员……如孙悟空,他一个人化身为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可能需要、可能遇到、可能忽视也可能轻慢的某个人。
他不停地换装,然后在每一段工作经历中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反省,如此一来,整本书就像一出“独角戏”,展现的是他焦躁难耐、起伏不定的内心图景。这情形很像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挪威作家约恩·福瑟在《有人将至》里面写到的大海的隐喻。
同是自传体非虚构,胡安焉却不似莫华杰一般袒露自己真正的心路历程。他很少暴露职业生活之外的自己,他克制而冷静地、尽量平实而不抒情地写自己的经历——作为读者,我们与他的同频共情也更多地在于此:面对生活和自我,他不相信煽情和卖惨,也不认可贫穷而漂泊就是人生的失败。
他用阅读学来的智慧,用写作培养的观察者心态,旁观、自省,恪守无愧于心的道德底线。尽管他也写自己的愤怒、羞耻和报复心,但他更珍视自己的三观,珍视自设的道德显微镜下的自己。他既主体又客体、既内部又外部、既自我又群体,因而他的书显现了“底层写作”确实无法定义的文学性和残酷的诗意,也显现了大时代中一个微观主体四处游荡的道德印记。
英国社会学家保罗·科利尔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认为,人类历史进展到了地理、教育、伦理因素日益撕裂社会肌体的程度,在这种撕裂之下,各个阶层都产生了“受害者”心理,产生了新的焦虑、恐惧,乃至绝望。而要想化解焦虑、消除绝望,主导人类生活的三个组织:国家、企业和家庭,都需要重建“互惠”式道德,践行开明的自利。唯其如此,人才能从自己经由国籍、工作、血缘确认的身份中重新获得被尊重感。
而另一位英国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则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说:“工作是决定社会地位和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在一个擅长分类并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是所有其他社会生活的锚点……工作类型也定义了人们应该匹配的生活标准,定义了他们应当与谁为伍,应当与谁划清界限。职业生涯标记了人生的旅程,是回溯人生成败最重要的记录,是自信与彷徨、自满与自责、骄傲与耻辱的主要源头。”
从《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我”一直在做有个性的好人,他的不妥协不乡愿不违心,只是为了找到适合自己的理想环境,确认自我的身份归属,当然,对此种愿望的虚妄他也有足够清醒的认知,因而他借用伍尔夫的话,将自己在伤痛和挣扎中度过的日子归纳为“伟大的失意”——一个大时代背景下无名的理想主义者的伟大的失意。
幸亏这种失意最后的落脚点是写作——文学也的确适合忧郁的失意者安营扎寨。从书里看,在走马灯般地换工作中,别说他的自我无处安放,作为读者,我们都无法安放他——若不是白纸黑字的确凿,他的追寻和我们对他的关注都会何其茫然而辛苦!
也正是因为如此,胡安焉变成了与众不同的“打工人”,当然,这也未尝不是他与文学的互为因果:文能穷人、文亦养人。而且,从他密集的述说中偶尔荡开的笔墨看——比如他写到的快递员飞哥、自行车店老板Y,都让人过目不忘——文学职业应该是可以安放他的。
当然,安放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文学总是有这样的错位:有生活的没技巧,有技巧的没生活。而如果二者在想象力的驾驭下巧妙结合,那作品就在金线以上了,甚至,可以走在靠近经典的路上。

《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著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3年3月
《窑变》:世无不变,唯变不变
跟莫华杰和胡安焉相比,李清源的文学梦想之路更顺遂。学中医出身的他,写作也是非科班,但他的虚构能力和文字天分让他一出手就得到了专业圈的认可。此后,他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一边写历史,一边写现实。写历史的时候他注重回到历史现场的“像”,语言、氛围、环境、知识,都不露怯;写现实的时候,他注重与生活同步的“像”,人情冷暖、所思所想都不隔。
表面看,他从来没有直接写过自己,但其实每一部小说里都有一个被打碎、被变形、被显影的自己,当然更有他潜心阅读、研究、致敬的文本,比如《红楼梦》《史记》等等的印记。而随着他对自己的打磨日益精进,他的小说创作在量变后发生了更大的质变,这种质变的完整呈现即是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窑变》。
这是一部胸中有大沟壑的作品,既有书写历史的雄心,更有记录现实的抱负。他抓住“钧瓷”这个核心,以要年纪事的结构,写中原古镇神垕镇的翟家六代人,在中国历史上五个无法绕过的年份:1898、1901、1910、1930、1957因复烧钧瓷发生的故事。如此设置,看上去是写家族往事,其实更要写出来的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流变,是历史变迁和时代转换之下人的命运,这种命运要跟今天的我们相关。
作为编辑和读者,看到这样的结构总是先要为作家捏一把汗。小说要从人间烟火中见时代风云,从爱恨情仇中感人性多变,从饮食男女中品造化弄人,尤其是,在读史大国、家族叙事泛滥的当下,小说要从平常中来,到非同寻常中去,谈何容易!其间的分寸拿捏又何其考验作家的境界与见识!
说起来,文学几乎就是眼高手低的试炼场,那么多经典挡在面前,那么多戏剧性铺展在面前,每一步都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即便做到了,还是“文无第一”。所幸,李清源做到了,做得稳健从容、外圆内方。李佩甫说他的小说是裹了丝绸的刀子,古雅中自有锋芒,诚哉斯言。
一般来说,没有完美的长篇小说,即便是《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包法利夫人》,也能挑出或多或少的毛病。一个有足够长度和容量的小说,如胃一般需要消化各种素材的小说,太过精细没有粗粝感,太过严谨没有天真气,审美上也并不一定就高级。
《窑变》当然也有不完美之处,但应当说,经过七年打磨、三易其稿之后,李清源对这个小说的把握已经臻于能力的极限,而这种“臻于”,已足以让这个小说的气象、格局、面貌不输于绝大部分当代作品,放在历史纵线中衡量也够分量,更不逊于很多所谓著名作家。
作家在这样一个历史跨度大、人物众多且命运多变、需要深厚钧瓷文化学养的小说中,体现出了中原作家俯首劳作般的细密诚实,也展现出生活阔大多艰熏陶出来的智慧和狡黠。看得出来,他活得通透豁达,写得匠心深沉。
书中,他将人物的爱与死写得尤其动人。爱得热烈的,心里也藏着不戳破真相的隐忍;爱得矜持的,心里却有死生一处的誓言。活得快意恩仇的,死得寂寞凄凉;活得憋屈安静的,死得却泼辣豪迈。她们“胜却人间无数”,他们“碧海青天夜夜心”。窑变,瓷变,世事变,人变,运变,情变,“世无不变,唯变不变”。然而,贪嗔痴恨爱恶欲不变,天不变,道亦不变。
李清源无比笃定地扎根在变化中,写人性如钧瓷一般,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写命运如窑变一般,七分天工,三分人巧。他超越了生活之苦和自我最初连接时候的笑泪歌哭,也不想一味地跟学会了思考和反省的自我周旋,他选择面向语言、面向经典,面向更多的命运,面向更幽深的人性,面向“文章千古事”。这种皓首穷经的“苦”,未尝不是最值得追求的“美学幸福”。
最近因为一首歌被更多人知道名字的传奇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据说是毛姆小说《刀锋》的主人公拉里的原型,他不断探索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部大书。有评价说,是他赋予了哲学谦卑的品质,“我知道这就是世界。我知道我身处世间”,因而他的哲学虽然难读,却无处不在日常中。他有两句名言一直广为人知:语言的界限即是世界的界限。不可言说之事,必将无言以对——很哲学,也很文学。
然而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他在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的时候打的比方,他说:哲学就是给苍蝇指出逃出捕蝇瓶的道路。据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做过一个实验,把一个敞口玻璃瓶横放在架子上,然后在瓶底打上一束光,之后,辛勤的蜜蜂都奄奄一息地聚集在瓶底,而苍蝇们,在几次碰壁之后,开始向其他方向左冲右突,不再一心奔着最明亮的方向,最后,它们重获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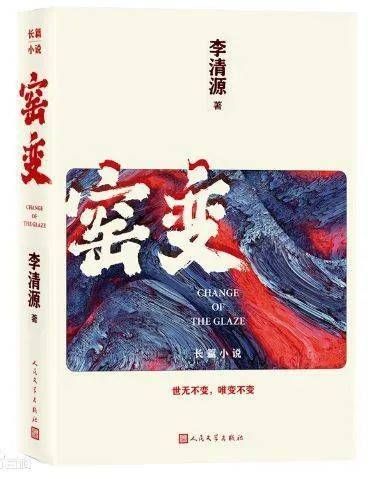
《窑变》,李清源/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6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付如初
相关推荐
5G手机到底有什么黑科技?
除了废话文学,互联网还有哪些野生文学?
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反战文学
深度分析Lyft和Uber招股书:同样是打车平台,到底有什么不同?
City Walk与“晃膀子”到底有啥不一样?
从“废话文学”到“鬼打墙文学”:浅析网络流行用语的排浪式消费
抖音上的“卑微文学”是个什么梗?数万人做“舔狗”,播放量超5.3亿次
迪士尼用AI做海报?好莱坞到底在紧张什么?
微信又改版,公号可以查“死忠粉”,到底有什么价值?
用意念打字、让阿凡达成真,脑机接口到底有多少花样“玩”法?
网址: 文学对他们,到底有什么“用”? http://m.xishuta.com/newsview94124.html